她现在这个工作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找的,她的学历和工作履历十分出色,所以并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接到了offer。那时刚过完年,我陪她去公司面试,坐在楼下的咖啡店等她。我在咖啡店坐了整整一个下午,她来的时候路灯已经亮起来了,我的咖啡也早已见底。她十分兴奋,小跑着到我身边,激动地拍打我的肩膀,我知道她成功了。
她入职后就争取到了一个颇有前景的项目,她兴奋地连做了三天方案,每天几乎只睡两三个小时,但却看不出多少疲惫,只有黑眼圈证明着她熬了夜。最后项目顺利落地,我们约好一起庆祝,在一个周末短暂地出游,在将要入春的海边支起了一堆篝火,聆听着寂静的海与爆鸣的火焰。一只灰色的海鸟随着海浪翻涌而来,整个世界被墨蓝浸透,我们的影子随着篝火与离岸风跳动。我感到胸中涌出海洋般无限的诗意,但我不会写诗,于是我只能摆弄着相机,希望此时的诗意能够兑现出某种形式的艺术。不知是因我许久的沉默还是忧悒的海的氛围,她一句话都没有说,当我跟她分享我拍的照片时,她也十分冷漠,草草看过几眼,便继续她眼神的游弋。我知道她又到了抑郁期,于是也不再说什么,只告诉她,我们的庆功旅游,开心一点,不要想太多。
我吃完了碗里的饭,转头望向窗外,似乎感觉那天海边的墨蓝色从记忆中渗漏出来,将今天也染上色。

那次旅行草草收尾,她后来向我表达了歉意。我对于那次旅行在一段时间内颇有介怀,于是在她又一次躁狂期转抑郁期时,我对她说了些重话,这毫无疑问地加剧了她的抑郁。我们吵了一架后我便回了自己家,两天后回来发现锅碗几乎没怎么动,只有一锅剩了层底的粥,也没有外卖袋子的痕迹,两三天时间,她似乎没怎么吃饭。我回来时她还躺在床上,药瓶子打翻在床边,几粒白色的药洒落在床头柜上。她没有睡着,双眼通红地望着我。我将散落的药片拾起,把药瓶放回原处,转身走出卧室,捡起躺在水池子中的一个杯子,冲洗干净,饮水机没有水,我把我在路上买的矿泉水倒进杯子,走进卧室。
“对不起。”
“对不起。”
我们两个几乎同时开口。
我不知道她那天尝没尝出那杯水里的眼泪味道,那个味道此刻正在我的身体里流淌,但我的脸上并没有眼泪滑落。
卧室里黑着灯,她应该是躺下了。她只吃了一点饭。我知道她是因为抑郁期没有食欲,但我现在似乎才意识到,我并没有做她喜欢吃的菜。或许我做了她喜欢吃的菜,她还能多吃点,我在心里懊悔。她很喜欢做饭,做得很好吃,相比之下我显得没什么厨艺天分。在她病情较轻的时候,家里一般都是她做饭,所以我的心里也没装着什么菜谱,只是按照我的观念,每当她抑郁期时,就给她熬粥、煮面,我以为这些吃食清淡好吸收,但或许她看见喜欢吃的菜会比看见这些寡淡无味的东西更有食欲。
我走进卧室,轻轻拉开椅子,翻了翻同事在微信上发来的文件,作了简单的回复,才想起来自己已经跟领导请了年假,除了这两次旷工,还有四天的休息时间。我坐在椅子上琢磨自己这几天该如何释放一下,然而我想出来的每一项活动似乎都有不去做的理由。床上传来响动,我轻声问她,睡着了吗,她哼了一声,我没有听清。其实我并不想知道她是否睡着了,我只是想和她说说话。我递给她水杯,坐到床上,轻轻按揉她的肩膀。
“辛苦了。这几天我放假,你要休息几天吗,我们可以出去散散心。”
“我还没想好,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上班。看看明天早上状态怎么样再说吧。”
我答了一句好,继续按揉她的身体,直到她睡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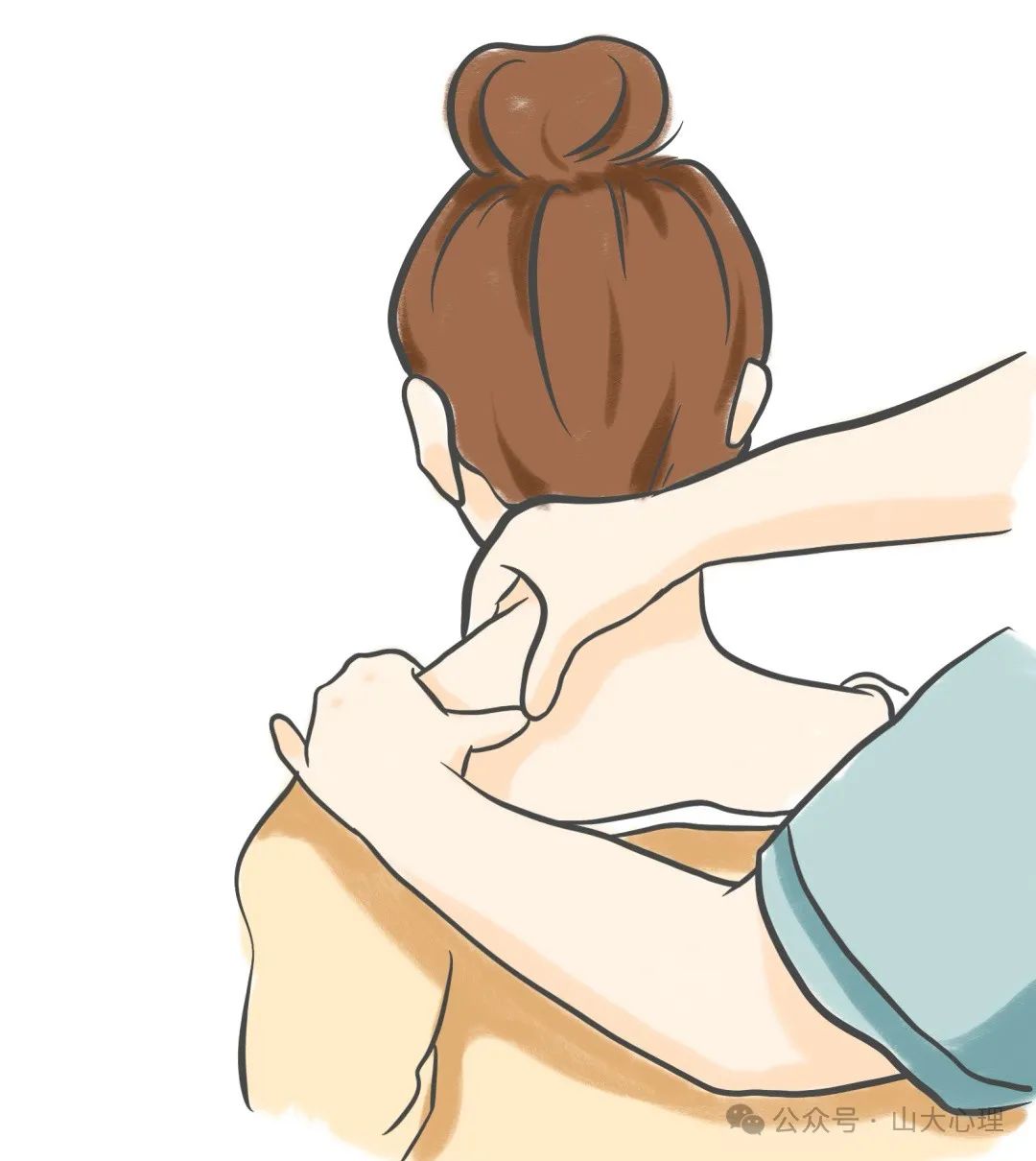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我醒来时她已经起床,我在床上闻到了煎蛋的油香味。我爬起来,感到自己胳膊有些酸痛,兴许是昨天晚上给她按摩得太久。她正在沙发上看电视,手里拿着半个梨,看到我起来,用头点了点餐桌的方向。餐桌上摆着煎鸡蛋,烤面包,酸奶。“我懒得给你夹起来了,家里的午餐肉都吃完了,没有肉了,你就凑活吃点吧。”她的声音中带着梨的脆爽。“不去上班吗?”我问道。“领导奖励我休息一天。”“奖励?啊?”我有些懵。“我拿下昨天的项目了,领导说我准备得很充分,让我来做那个项目。”我感到惊喜,同时又十分疑惑为什么昨天晚上她回来十分沮丧,我以为她竞争项目失败了。我十分想问,但我十分清楚,对待双相患者,不能把自己想问的都问出来。
她又咬了一口梨,说道:“昨天晚上我下班坐公交车回来,在车上看到一个小女孩,牵着她妈妈的手,问她妈妈:‘我们还会回来吗?爸爸怎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呀?’,她妈妈没有说话。我想起我小时候了,也是那样一个晚上,我坐在车里,路灯透过车窗,在我的脸上摇摇晃晃,我离开了我小时候的家。”
我恍然大悟,她原来是因为路上看到了这一幕,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,才会表现得那样低落。我知道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的,她的父母在她5岁时就离了婚,她跟着她妈妈生活。她的妈妈不算是一个坚强的人,身体也不算硬朗,但为了女儿,也应付了二十年的艰辛。她曾跟我说,她妈妈对她一直很严格,从学习到生活,但自从她生病后,她妈妈愈发变得柔软。我在见她妈妈时也深有体会。那天是程一洋将我和她妈妈约到一起,她妈妈很年轻,那天还化了淡妆,只是眼中的血丝并没有被遮住。她妈妈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,在我面前也没有摆出一个长辈的架子。我不断地表示着照顾好她女儿的决心,程一洋也在旁边帮腔,有意无意地夸我两句。她妈妈总以微笑回应,只是那微笑中总带有几分内疚。
她是在我们那次吵架和好后与我聊起那些往事的。那天我回到家,看到她蜷缩在床上,心中产生无限的自责。大概是那天起,我真正地爱上了她,或许是因为我的心脏在看到她后确确实实地抽疼了许久。我为她做了些吃的,说了很多道歉的话,但她多数时候仍然会背对着我。她的痛苦并没有随着我的归来而减轻,或者说,我也不知道在我离家的那两天里她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。一天过去,我实在无法坐视她颤抖的手,痉挛的身体和不定时的干呕,我提出要带她去医院,她却喊出了巨大的声音:
“我不去!我不想有病!懂了吗!”

那时我才明白,世界是一个由误会组成的圈套。别人的关心和怜爱,或许会成为她的病耻感,这不是因为人性皆恶,而是自卑的悲剧。
那天夜里,我趁她睡着,把她背到了医院。我并不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人,但我那天还是把她背到了医院。她挂水挂到日出后才醒,我早已靠着椅背睡着,她后来说,那是她第一次觉得我真的爱她。那天,她和我说了很多她的往事,包括她的原生家庭。
“我们去踏青吧,今天天气不错。”
“好,想去哪儿?”
“去莲石湖吧,听说那踏青不错。”
我们到莲石湖时,太阳已经躺在西山上边。世间满是金黄,我们踏了一个日落的晚青。工作日游人不多,几个刚放学的小朋友缠着唯一一个有风筝的小伙伴,他们在草坡上追逐嬉闹,湖水在不远处转着圈消磨时光,等待下一个日出。
我们走到一棵树下,那里趴着一只猫,身上沾着柳絮和灰尘。
“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吓着你了?”我们坐在那只猫的身前,她对我说。
“还好吧,我就是以为你项目申请不顺利。”我回头看着那只猫,那只猫也盯着我。
“那个小女孩,真的很像我。或许我的病,跟我的家庭关系不小吧。”
“那我觉得那个小女孩未来应该也会很出色。”
“你又说好话。”
不知什么时候,我们身后的那只猫偷摸摸地走掉了。
一年后,我们结婚了。药瓶依然堆满了我们的床头柜,但旁边多摆了一个画册。那是我强烈要求她摆上的。画册的封面是一只猫,我每次看到那幅画中的猫,总觉得有些熟悉,或许就是那只春日夕阳下偷偷溜走的猫,也或许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,趴在CBD的花坛边的那只奄奄一息的猫。